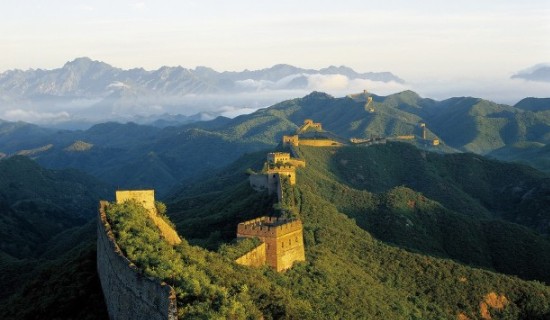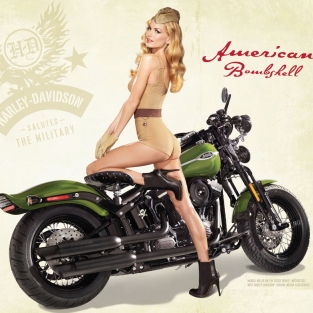连载(七):一名资深空姐眼中的民航业变迁
|
我们的驻地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第十六区的一栋三层小楼里,听说是清朝政府办洋务时留下的房子。这里地处巴黎布洛尼森林和凯旋门附近,街区很古老也很幽静。 这里不仅是我们机组的驻地,也是办事处的办公场所,除了办公用房,几乎没有几间房间可供我们居住。我们6名乘务员合住在一个大房间里,顺着墙边摆满了床位,拥挤程度可想而知。小楼里能用于公共交往的场所只有一间电视房和地下室的厨房、餐厅。闲暇时,我们只能在楼前的庭院里活动。记得刚入住的时候,办事处经理提醒我们在院子里散步时不要大声喧哗,以免引起邻居的不满。但这一嘱咐常常被我们遗忘。 巴黎与北京的时差有6到7个小时,我们的作息时间显然与当地居民不同。有一次,我们早早地起床,想到布洛尼森林公园去散步。从小院的窗口望出去,发现大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。我们不敢贸然外出,只好在院子里散步闲聊。没想到,一句“安静点儿”的法语从我们头顶上飘来。我抬头一看,隔壁的一位女士很不满地在向我们喊话。顿时我想起了经理的提醒,类似的事情可以说经常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。当地人不理解,明明只能供一家人居住的小楼为什么要住上几十个人,中国人为什么有大声说话的习惯。 刚刚开通国际航线时,机组的海外生活基本上是围绕着独立的小院和小楼展开的。我们的生活自成体系:公司派出的厨师为我们准备中餐,勤务员为我们打扫卫生。小院的围墙成为天然的屏障,将我们与当地的生活分隔开来。我们过着自娱自乐的生活,帮厨、搞卫生、学外语、体育锻炼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。由于语言的障碍、生活习惯和文化的阻隔,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外事纪律让我们很难了解到当地民众的真实生活。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找到了观察当地社会的有效办法。由于供给制的原因,我们没有收入来源,也就不可能进行独立的旅游消费。但这并没有难倒我们,步行旅游是我们当时最为流行的做法之一。在治安环境良好的国家里,我们的双脚几乎走遍了驻地附近的大街小巷。借助这双“铁脚板”,我们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,也了解了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,开阔了眼界,增长了见识。 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,我们在亚洲和非洲的驻外生活另有一番趣味。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我们当时飞往非洲的唯一目的地。这儿的天气并非我想象中那么炎热,记得那时,每天晚上都有一场大雨,天亮后就开始放晴。小院里的花草五颜六色,树木郁郁葱葱。邻居的小孩经常到我们院子里嬉戏玩耍,给我们做勤杂工的当地人热情友好,他们常常用半生不熟的中文与我们交流。帮助办事处到当地市场采购生活物资,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当地居民的生活,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。 卡拉奇是我们最初通往欧洲的一个中途站,每年我们都要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,炎热和缺水常常困扰着我们。但是驻地的几栋小楼与庭院蜿蜒相连,居住的空间和活动的场所与其他国家的驻地相比宽敞得多。我们饭后散步、打乒乓球、聊天,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好,给枯燥的驻外生活平添了一些乐趣。 我们的航线将各个驻地的小院串联在一起,在异国的小院里休整后,我们又飞向另一个驻地。每一次,我们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到这里,又载着当地的见闻和收获飞回祖国。小院是我们的家,是我们旅途劳顿后身心放松的场所,也是我们那个年代身处异国他乡的港湾。
(责任编辑:高沛勇) |
- 上一篇:“五一”飞行不用愁 空姐教您如何轻松乘机
- 下一篇: 东航浙江凌燕特色航班之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
|
|
||||||
|
|
||||||
|
|